順便感謝家中忠狗 Oreo 動人的演出!)
C曾講過,在看到兩人進行英文對話時,總會讓她想到托福光碟中的場景。而目前正在學習韓文的她,卻像是被溫暖的愛情所擁抱一般。未能被韓文中愛情氛圍包圍的我,反而琢磨起西班牙文,和艱難文法一起陪伴著我的是 — 足球,阿莫多瓦(Pedro Almodóvar)和”哈哈哈”的西班牙文課。
當一般的女孩,流連在百貨公司的時尚服飾店,精心挑選當季新潮流行的衣裝,平日不修邊幅的我,卻會衝進足球俱樂部的專賣店,購買印有”皇家馬德里” (Real Madrid),不怎麼具有時尚風的圍巾和球衣。雖然對路上行人偶爾”這個女人似乎缺少一些女人味”的評頭論足感到些微的抱歉,但卻仍舊我行我素地暗自發誓,總有一天要能聽懂球賽中,西班牙文球評在進球時中氣十足地大喊:
“g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al!!!!”
以外的評論。
而阿莫多瓦介入我的西班牙文世界,就像他在西班牙的電影界地位一般不可分割。在機場聽到用西班牙文展開的對話,讓我回憶起阿莫多瓦電影裡的女性角色,總是絮絮叨叨像是家常便話般談著自己受盡委屈的人生。我最喜愛的一部作品,”悄悄告訴她” (Talk to Her/Hable con Ella),在片中更是穿插由古巴樂手 Caetano Veloso 改編自墨西哥歌謠的鴿子之歌(cucurrucucu paloma)[註1],宛如流放詩人聶魯達筆下的詩意盡情在歌中流瀉,西班牙文的美麗在歌中與阿莫多瓦的影像結合,既是哀愁呢喃,亦是惆悵深嘆。
雖然在目前的科學文獻中,或許缺乏因為學習另一種語言而徹底改變人生這樣的劇烈的例子。但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[註2]卻也指出人類不會因為母語文法上的限制,而無法體會了解”享受吧!一個人的旅行”(Eat, Pray, Love)裡意大利文中”Bel far niente”(無所事事之美)的境界。文法對於語言的束縛,就像英國紳士總要盛裝出席下午茶聚會,習慣從小生長在具有陰性和陽性詞性的言語裡,在言談之間免不了多透露了些訊息。比如說,談到昨晚的去向,中國男人可能輕描淡寫地講:”和同伴聊了一個晚上”。西班牙男人卻不由自主地說:”Hablé con mi compañera toda la noche.” 無意中就講出了陰性的同伴用法,透露了和女同伴共度一晚的外遇先機。
當然,未能讓想要偷情的西班牙男人得逞的語言,也不會是全然構成”哈哈哈”的西班牙文課全部要素。記得,多年前曾學習德文的妹妹,相當欣羨的告訴我,當身處德文課與拗口的德文發音艱苦奮戰時,隔壁西班牙文教室總是傳來一陣又一陣爽朗的笑聲。當時聽來,也是”哈哈哈”的不以為意,甚至覺得怎會有講來這麼快樂的語言呢?等到自己上了西班牙文課,課堂上”哈哈哈”的情況也不少,不過通常是在與同學練習剛學到的句型對話時:
(情境: 用剛會用的西班牙文進行電話對話)
R: “¿Digame?” (請說?)
S: “¿Esta Rene?” (Rene 在嗎?)
R:”Si, Soy Yo.”(是,我是)
(接下來一陣沉默…..)
S:(轉換成中文)怎麼辦接下來還沒教到…
(兩人開始不好意思的哈哈大笑)
R:”那就 Adiós (再見) 吧! “
S: “Adiós~”
即使在初級班上演著史上最短的電話對話,也不阻撓隔壁中級班傳來撼動教室的如雷笑聲,不禁要讓人懷疑,西班牙文難道是會讓人愈學愈感到歡樂的語言嗎?雖然不抱有因為學習西班牙文,而從此改頭換面成為擁有積極樂觀的人生。目前的我,就像電影裡”Shall We Dance?”李察吉爾(Richard Gere)飾演的 John,一開始因為珍妮佛羅佩斯(Jennifer Lopez)飾演的 Paulina 在舞蹈教室窗口憂鬱而美麗的臉,而報名了跳舞課,卻在學習中俯拾了更大的樂趣。
所以當老師是正統的馬德里人,上西班牙文課的情形是怎麼樣的呢?結果是要經常忍受老師講中文時調音。有一次,我的西班牙文老師,Profesor J,要用中文解釋”lógica”的意思,先是講”囉及”,後來自己想想不對,又試著講”裸機”,”羅紀”,”囉機”。最後大家聽到快哭笑不得,只好試著糾正他:
“邏輯”。
但,Profesor J 也是有扳回一成的時候,當同學們在課堂上一個個練習時,一位女同學一個不小心把”¡Que Hambre Tengo!”(我很餓)念成了 “¡Que Hombre Tengo!”(我想要男人)。只見 Profesor J 略感抱歉,又愛莫能助地笑著糾正她:”你想要男人呀?”
有一位能夠用比較中文的方式來教導西班牙文的老師已經很難得了。比如說,Profesor J 在教我們 “我喜歡 xxx”的句型時,就會告訴我們,在西班牙文其實是”xxx給我喜歡的感覺”(聽到這裡,就更喜歡西班牙文了 ! 還真是個不強調自我的語言呀 !),所以xxx才是句子的主詞,除了要加上”我”的受詞代名詞 Me,喜歡的動詞變化(Gusta,Gustan) 也必須跟著喜歡的名詞(單,複數)來做變動。
雖然,目前已經為了要記憶名詞的陰陽性,以及因為詞性不同,定冠詞和形容詞的變化,而弄得七葷八素。未來,正式跟動詞變化交手時,才會真正身處在阿鼻地獄中吧。但即使如此,對於會把標點符號顛倒放的語言,還是很想大聲的說 :
” ¡ Me Gusta Estudiar Español !”
” I Like to Study Spanish!”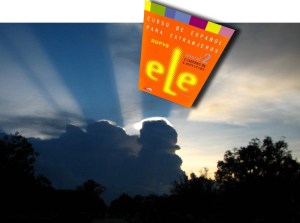
背景是在吳哥窟拍攝到的耶穌光!)
[註1] 因為太喜歡這首歌了,特別收了連結。有興趣的人可以聽聽看囉! Follow Me To 天籟美聲!
[註2] “Does Your Language Shape How You Think?” 這篇文章相當有趣,一開始先對 Benjamin Lee Whorf 所提出的母語限制人了解文法中缺乏的關念進行反駁,文中更舉了不少的例子,語言的結構卻也能深植超乎表達的能力。其中對同身為路癡的我感到不可思議的,應該是文中提到澳洲土著 Guugu Yimithirr 的語言中是利用東西南北這樣的絕對方位來表達自己的位置,而不是我們一般在語言用的前後左右相對方位。而說這種土著語言的好處,就是大為減低迷路的能力。是不是很神奇呢? :D
